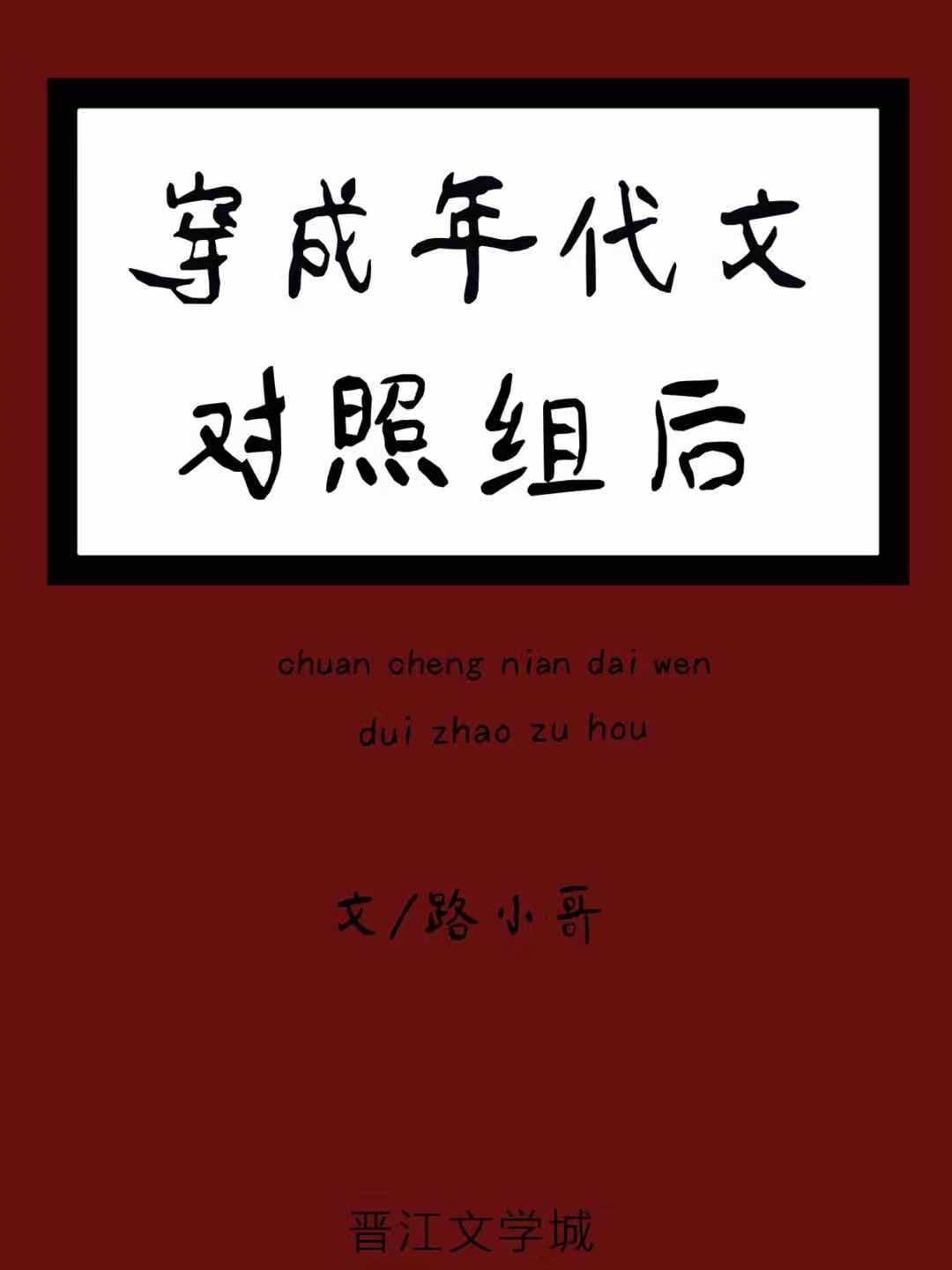妙笔文学网>道德颂歌曲 > 第40页(第1页)
第40页(第1页)
旨邑看不见水荆秋,无法想象他说这番话的模样。他在费力地表现他的彷徨与痛苦,无奈与罪孽,语气仿佛“阿弥陀佛,出家人慈悲为本”。她并没兴趣看他的表演,在她身怀一双孩子的时候,她应该是主角,所有悲伤的绝望的感天动地的台词,应该成为她的独自。水荆秋表演越动情,越泄露了心底最本质的想法,她捕捉到那难以掩藏的父子情深,那难以掩藏的父子情深,正是他欲抛下一双孩子的潜在原因。她不想歌颂他此时的父爱,只是更为腹中的孩子感到冤屈与不平,嫉妒他在地上奔跑了多年的儿子,他不知道他有两个兄弟(姐妹),正孕育在父亲的情人的子宫。缓慢平和的交谈,没有谁的音调高出“阿弥陀佛”,似乎双方都在让步,反而承让出使人不知所措的巨大空间。然而,她一想到,她的一双孩子将扔进装满胎尸、鲜血模糊的垃圾桶,心就难过,抽痛,疯狂。母鸡尚有本能在危险时将小鸡护在翅膀底下,她绝不可能目睹一双孩子血肉模糊的惨状。她可以没有男人,但不能没有孩子。她感觉到,这是一场战争,和水荆秋,和梅卡玛,和自己的遭遇之间一场战争。我们来看旨邑这同样困苦的一天。水荆秋打来电话问旨邑堕过几次胎(仿佛他开始为她考虑了),旨邑感觉幸福的光芒从阴云中透射,周身温暖。她如实相告,她的子宫绝不能再承受堕胎之难。水荆秋苦叹数声。她在这一刻感受到水荆秋的动摇与慈悲,过去播种在心底的爱,发出同情之芽。然而,周围土壤及环境并不适合生长同情,那嫩芽出土即死。她的意志与信念已经长成一棵大树,水荆秋知道,他这只蚍蜉无力撼动它。沉寂的等待中,旨邑的眼前不断幻化出关于孩子的美好画面,而现实总是如一盆污水将它弄脏。翌日,水荆秋又打来电话,她感觉他面目狰狞,满嘴犬牙交错,狼牙暴突,两眼猩红,万分凶狠地逼视她、威胁她,浑身长毛竖起,人性全失,朝她咆哮怒吼,仿佛要以此吓退她,征服她:“四十多年来还没人能牵着我的鼻子走。你想要孩子我知道,你的孩子归你,我身边的孩子谁也不许碰……”水荆秋突然不“呃”了,十分流畅地说出这几句话。旨邑看到他从一棵树跃向另一棵树,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,时而两腿站立,时而四肢着地,或者双手撼树,让纷纷落叶与沙沙声响为他呐喊助威。“天啊!”她惊呼一声,只觉天旋地转,“水荆秋,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?”她的心挨他这一重击,当下痛得缩成一团。她从没想过她和他之间会诞生恶人和善人,她从没想过要以善恶来对一件事情作结论,也没想过高原时探进她身体的那只温暖的手,竟来自于一个恶人。“昨天下班回家,看见儿子把他和他爸爸妈妈的名字写在围墙上,我心如刀割。我想清楚了,就算是十个孩子我也不换这一个,你生了我也不会认。你要恨就恨吧。”他说。“天啊!”她浑身哆嗦,握电话的右手抖得特别厉害,“天啊!”她连续喊了几声,左手绝望地停在腹部(她的一双孩子帮不了她),说不出除此之外的任何字眼。对她来说,世界上任何噩耗都抵不上他这句“这个恶人我当定了”的话。她强撑住不让自己晕倒,牙齿打冷颤似的发出磕碰的声响,张开嘴大口喘气,牙齿将舌头磕出了血,但她对此毫无知觉。她站起来,没迈动半步,复坐下来,茫然四顾。她在这一瞬间老了。迟钝。呆滞。步履蹒跚。被扑灭了春天的最后一丝生气。“知识分子+佛教徒=恶人。”意识重回大脑,体内暖意苏醒时,她首先想到这个等式(无疑,是水荆秋自己填写了等号后面的结果)。“你还信佛吗?”她无法思考太多。左手轻抚腹部。她不能大喊大叫,不能吓坏那一双同样可怜的孩子。“我没有办法,我什么都管不了。我只要和我现在的儿子在一起!”他完全是穷途末路的冲撞。“你是佛教徒,多年烧香拜佛诚心为善,现在当了恶人,怎么向佛祖交待。”她见他连多年的信仰部不要了(这不仅仅是与信仰有关的事),进一步追问。他对此避而不答,只是说:“随你怎么着,我等着,即便是死亡。”她说:“伪信徒是没有资格死的。你的死不能解决我的问题。我的死能解决所有问题。记住,你要想死一定要学日本人切腹,因为肝肾以及周围的脂肪是感情和生命的寓所,你的灵魂寓于腹部。如果你有灵魂的话。”她话未讲完,他粗鲁地挂了电话,她脑子里活跃的话语东突西撞,它们是她的子弹,渴望射向他的胸膛。她给他拨过去,而他已关机。“教授,我们来谈谈善恶。”她很想对他这么说。旨邑在阳台横躺,死了一般。湘江死了,尸体卧在山脚下。风景也死了,只剩下焦黄的脸色。过去的两天时间,旨邑和水荆秋越谈越僵。她没耐心,更无哀求,以硬碰硬。水荆秋的意思是,只要她坚持生孩子,他不会再和她有任何联系,哪怕有朝一日必须面对法庭。她说她把三条人命都给他。他无所谓。他的决绝像一把利剑刺中她的心窝。她说她要以恶制恶。他无所谓。把手机一关,躲起来了。关于水荆秋的温文尔雅,竟是幻觉。旨邑的仇恨比刀锋更利,愤怒使她变成一头凶猛的野兽,她想立刻扑上去撕咬他,撕咬他的灵魂,撕咬他的良心,撕咬他作为知识分子的那一部分。旨邑在阳台横躺,死了一般。一个声音悲悯,一个声音仇恨,它们在天空中碰撞出强光,映照她失血的脸。她麻木不仁。一个人漂浮在黑夜的海,没有亮光。水荆秋的声音像闪电划破黑暗:“这个恶人我当定了。”“就算十个孩子我也不换这一个。你生了我也不会认。”“我只要和我现在的儿子在一起。”“随你怎么着,我等着,即便是死亡。”被他的话鞭打,她的知觉醒了。他的话鞭打她,她感到清晰地痛。他的话如荆棘条,轮流抽打她的灵魂,她的肉体,它们沾着她的血肉,她的痛苦,变得越来越结实,越来越明亮,越来越臃肿,最后像一条圆睁双目的毒蛇,将她紧缠得透不过气,喊不出声,哭不出泪,她双手扯住这毒蛇冰冷的肉体,别过脸去。这冰冷的蛇是他的舌头,他黏滑的舌头,曾是蜜,是花,是春天,是可口的菜肴,它温暖体贴,它进退有方,它扫荡她的灵魂。她依着十字架站直了身体,在人群中寻找他的脸。那张脸肯定变了,或者戴上了面具,或者摘下了面具(她不能认出来),混在人群中看她的苦难,毫不动容。她努力回忆他的样子。他比江水混浊的脸色。他比斑驳古画更模糊的温和。他如鸿毛般沉重的身体。他或许正携妻带子,夹在这沸腾人群中享受生活的意外与快慰。梅卡玛是那样挺拔的女人,面色柔和,目光锐利。他那世上的儿子,四肢健全,没有兔唇与豁牙,没有小儿麻痹症留下的遗憾,没有智障患者的散漫眼神,他是一条早熟的小狼狗。她左手停在腹部。她摸到了他的孩子——不,是她自己的孩子(他不要他们)。他们只是b超图上的两颗小黑点,她突然觉得他们好重,仿佛再走几步便将摔倒在地。“做母亲是个灾难。我不想歌颂它。”她挣扎着说出这样的话,左手停在腹部,禁不住泪流满面。她感到一双孩子在对她说:“妈妈,我们相依为命。”她看见那推婴儿车的母亲和扭头笑看母亲的孩子。教授的确躲起来了。水荆秋教授为何选择躲起来。她的小跳蚤弄不明白。她无望地打他的电话,意外地接通了,却不知从何说起——因为,该谈的皆已谈尽。
请勿开启浏览器阅读模式,否则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。
相邻推荐:极寒天灾温泉街模拟经营 和顶流结婚后上了孕吐热搜 盛可以中短篇小说 无爱一身轻 快穿之黑化男主在我怀里哭唧唧 谁侵占了我 反穿之强下弱上 时间少女 火宅 三国神话世界 虐主文的NPC消极怠工了[快穿] 宝贝甜心收美男 那些穿成镶边女配的女孩们 开局捡到旅行水母[深海求生] 北妹 娘子一媚乱天下 娇弱npc拿了团宠剧本[无限] 水乳 救赎偏执怪物后被觊觎了 重生毒眼魔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