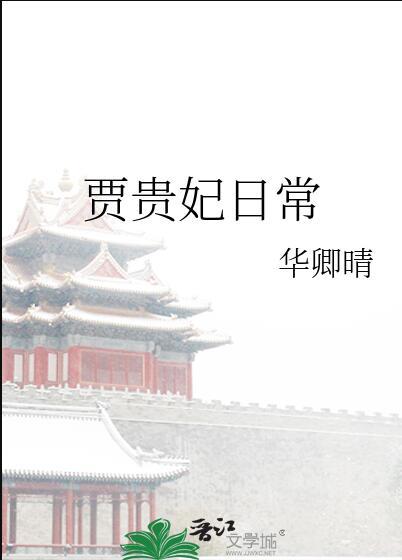妙笔文学网>黄金万两前一句怎么说 > 第80页(第1页)
第80页(第1页)
苏辞平淡道:“昭怀太子妃病入膏肓,殷大夫说已无可救药,至多还能再保两个月。陛下说,岛主与昭怀太子妃青梅竹马,这最后一面,端看岛主见是不见。”这最后一面本该辜薪池见,但萧尚醴与乐逾都心知,乐逾绝不会让辜薪池以身涉险。乐逾道:“乐某记得自己至今是南楚钦命要犯。”一离蓬莱岛入楚国境内,就给了楚国擒下他的缘由时机。苏辞一脸镇定,看向他道:“陛下说了,这最后一面,端看岛主见是不见。”苏辞敢上蓬莱岛,因为已针锋相对,两国为敌,反而不斩使者。楚帝的使者在蓬莱岛出了差池,蓬莱便要被迫与南楚有弥天大恨,不死不休的仇怨,这对蓬莱岛而言绝非益事。乐逾道:“见是不见,乐某明日会给你一个答复。稍后有船送明鉴使上岸。”苏辞却道:“小女子今日已疲惫了,有意再叨扰岛主一夜。”她是想打探蓬莱岛上的情景,乐逾却不惧她打探,也不多纠缠,随口道:“悉听尊便。”就送客了。蓬莱岛上整理出雅洁客室,装点洒扫,供楚帝的使者下榻。岛上的僮仆侍女,许多年纪还小,对苏辞的身份一知半解,也不知蓬莱岛与南楚朝廷间出了多少事,只是难得见生人,还是孤身一人到岛上的年轻女子,不住地偷偷望她。林宣却滴水不漏,亲自询问过苏辞饮食喜好,甚至主动提议她四处走走。蓬莱在南海上,地面温暖,落雪也不似锦京,雪片虽大,落地不多久就要融化,少有能积几日的大雪,更常有雨雪交加的情景。这日蓬莱岛上午后雪将融未融,她沿石径走上一片小丘,这里地势略高,可以看见方圆数里,别处都是青松,这里四周却是花树环绕,影影绰绰。枝干上没有花叶,披着小雪,别有一种清新。苏辞默想来时的路,片刻又摇头。来时船上门窗都被封住,她有心计时,可是足有半柱香时间在漩涡中辨别不清方向。不知蓬莱岛的船如何在几十里的大雾中找到路径。她心道:“罢了。”望向小丘下远远的溪水,花树中露出的精巧屋舍,居然看得出神,觉得这真算人间仙境。方才客室之中,以龙脑熏香,灵芝绛草为盆景。坐榻边铜炉燃炭,温暖如春。顶上吊的帘幕轻薄如烟,纱帐四角以四串硕大浑圆的珍珠坠子压住。细纱上并非刺绣,而是以笔墨绘制梅花。鹅黄色的薄纱被珠光映照,如同月光,漫天白梅飘洒,花蕊藏有暗香,放下纱幕就如同梅花落满一身。豪奢珍巧之处纵是比楚宫也差不了几分。海上蓬莱岛确实不逊于人间帝王家。小丘下林宣走来,应该是请苏辞去用晚膳。苏辞颔首,迎了上去。一个仆妇匆忙上来,慌张行礼,到林宣耳边说几句话。林宣面色立时变了,转过面向苏辞道歉,就先行离去。那仆妇跟他急急忙忙地走,只留下两个侍女。苏辞见她二人颇为好奇,便连两个侍女都遣散。蓬莱岛上大多是没有武功在身的人,自然听不见,她却听出一棵树后有细微呼吸声。待到人都散去,她走到树后,步伐极轻,果然见到一堆雪白。那雪白中的一团雪白是一件对幼童而言十分宽大的白狐皮披风,罩在人身上,远远望去与雪地一色。苏辞早就知道蓬莱岛主有位小公子,料想方才仆妇是来通报,小公子不见了,却不知这位小公子也溜出来偷偷观望客人。苏辞伸手拍那孩童,那孩童猛地抬起头来,她暗自惊心。那孩童不解地看她,反而披着狐裘踟躇上前,白裘衣,银靴子,黑发及肩,玉雪可爱。仿佛晴空霹雳照亮那孩童面容,稚嫩容貌竟与苏辞记得的某一位别无二致!她只觉背后一凉,那神情天差地别,可五官分明与……那位陛下……苏辞惯经风浪,也不禁心思混乱,为何蓬莱岛主的公子会与大楚天子如此相似,只能叫人认定他们必然是血亲。莫非陛下有流落在外的子嗣,却被蓬莱岛扣住以作人质?她保住镇定,那孩童却睁着一双灵动的眼睛看她,软软叫了声:“姐姐。”苏辞一回神,才见那孩童提着下摆沾到雪籽的狐裘,踮脚巴住她的手,将一块糖糕塞进她手里,道:“我要回去了,好姐姐,别告诉人你见过我!”蓬莱岛上这小公子原本爱看热闹些,却也乖巧听话,得到父亲为他易经伐髓之后,终日精力用不完,三四岁上就已经学着爬树翻墙,顽皮之处只比他父亲当年好上那么一点。好在他闹出事情会一个人认下,逃开了不多时就会回去找乳娘。含桃馆的侍女仆妇都当这回虚惊一场,他不说,苏辞心中疑窦丛生,更不会提起。次日清晨苏辞乘船离岛上岸,蓬莱岛上下竟没有人知道小公子送了楚帝的使者一块糖糕。这一日夜晚,岛上冷雨飞雪,海上波澜重重。一个温和端正,气色却很不好的男人提灯前行,裹在裘衣里,一反常态地步履匆匆,正是辜薪池。林宣追上,道:“先生,岛主在‘不追堂’……”辜薪池步伐忽然停下,蓬莱岛乐氏没有祠堂,“不追堂”便是祠堂。所谓不追,就是乐氏先祖告诫后人,前事不可追,也不必祭祀跪拜。不追堂常年封闭,其中陈列诸多先祖的遗物。即使辜薪池与乐逾亲密如手足,也不可入内。辜薪池缓缓道:“那我就在不追堂外等他出来。”他鲜少这样不容转圜,但乐逾要再度离岛赴锦京,辜薪池无论如何做不到赞同。尤其是明知乐逾这么做有一半是为他……辜薪池不能入南楚境内,可若是在唯一存世的亲人死前不能见她一面,听她说一句话,势必是一生的憾恨。几位年长的校书向他们二人望来,不知这师徒二人为什么起争执。林宣自小跟随这位先生,为使先生对他另眼相看,从小就把体面与礼仪放在心间,此时心一横,再难受也勉力一笑,只道:“先生纵然不为自己的身体思量,哪怕为我,思量一回呢。若是先生出了什么事,我该如何是好?”不追堂内,四面墙有三面挂满字画,一架架陈列架由地面连到屋顶,分先后堆满乐氏诸位先祖的手记遗物。当中四四方方一片空地,青铜灯架点满蜡烛,在那空地之间摆着一架七层的台案,每一层都摆放先人牌位。木台下一个黑衣的高大男人席地而坐,年纪不足四十,黑发间已掺杂银丝。堂内静而冷,不设炭火,没有木炭吱吱燃烧之声,却能听闻雨雪落在屋顶又滴落的水声。乐逾道:“我有一问,不知诸位谁能答我。”锦京之行该不该去?蓬莱岛上诸人都想劝阻他,可真正能劝阻他的人都已经在这里。烛火燃烧,将他的侧面映得更为深刻。他在此处不饮不食,盘膝而坐,长剑颀颀横在膝上,坐了良久,从白昼到深夜,对那堆成山的牌位道:“我舍弃正趣经已经三年。”自更夜园小宗师之战走火入魔以来,他再也没有动用过正趣经心法。每一次出剑,就更偏离正道一些。即使得到寒松寺外禅宗高僧传授“清心咒”,自己频频闭关,也压制不住杀念。内力越精进越是戾气深重,只要颀颀在手,就想大开杀戒,见血方休。他以手指拂拭颀颀寒锋,道:“好在小蛾降世,我已为人父,念及膝下稚子,我就能遏制杀念。否则……我再没有顾忌,没有退路。”唯有像“血衣龙王”那般以杀证道,只求成就宗师之后能重得心中安宁。指腹粗糙,剑光清如一泓水,在烛光中映亮他的眉眼。眼前墙上挂着乐游原手书,正是那一幅“狂以成名为竖子,达能退步即神仙。须知楚汉寻常事,我欲吹笙鹤背眠”。乐逾看了片刻,他狂以成名,却不能达而退步,沉默许久,猛然一拂袖。狂风席卷,那灯架上一排一排蜡烛尽数熄灭,青烟袅袅,室内转暗。乐逾望向高处乐游原的牌位,道:“想来你也不能答我。”太虚境中的青色身影不知是幻是真,如此多先祖,没有一个能阻止他。他提剑转身,走出空荡厅室。锦京一行在所难免。锦京真是他一生最多劫难处,陷入情劫,走火入魔,都是在那里。这一次杀念已成,蛊虫还在体内,再去锦京不知还要遇到什么劫难伤痛,可既然是命里的劫数,他就绝不会回避。就如同百年以前,时移世易,乐游原年及而立,闭门一个月,在冬夜里仗剑而起,舍弃辛苦求得的平静清修,扑入乱世风雪之中,去赴他的宿命。他迈步出门,内力震荡,不追堂大门在他身后撞上。将不绝的坠落声锁在他身后,斜飞疾来的雨雪沾上他衣袍头发,不追堂内,七层台上祖先牌位纷纷震落,一层层倒满一地。次日清晨,明鉴使苏辞与蓬莱岛主有约在先,明鉴司的车马都在此等候。细雪纷扬,到近午时,才见一只小舟渡海而来。无尽海浪自天边被那一只小舟分开,天高云白,海浪翻滚却如墨色,天海之间细雪几点白,都沾在舟上一个男人胸前衣襟上。他黑衣黑裘,腰悬长剑,虽披裘衣,衣下却是单袍,在海风中紧贴身躯,越发显得肩背宽阔,手臂有力,身材强健。苏辞抱琴一礼,道:“乐岛主。”相隔十里,风急浪涌,她的话声却凝而不散。乐逾道:“乐某要往锦京一行,却没说过与诸位同行。”声音低沉醇厚,语罢一声唿哨,忽听得不知何处来的蹄声,诸人眼前一花,只听见马嘶。蓬莱岛主弃舟踏浪,涉水而来,挽住一匹骏马,抚它颈项,爱惜道:“人间又见真乘黄。”竟是早安排了坐骑,那马果然一身黄色,颈背腰臀皆圆润矫健。乐逾连再会也不说,纵马奔去。
请勿开启浏览器阅读模式,否则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。
相邻推荐:不一样的规则怪谈[无限] 情敌死后为什么缠着我[穿书] 回南天+番外 在荒野求生综艺立娇软人设爆红了 带着淘宝去古代+番外 猎户家的漂亮哥儿(穿书) 修仙不如跳舞 快穿之我又有了 虚拟雄虫偶像[虫族] 重生八零,大嫂有空间 清穿之据说佟贵妃体弱多病 万人嫌和隐婚竹马上恋综后 爱意收集系统 当诸朝开始围观我的语文课[历史直播] 心机外室上位记 早点睡觉 缉凶西北荒 原来我该成仙呀 信了你的邪 龙君苏醒在星际